
2023年9月26日,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了“孙机先生学术追思会暨第五届中国古代服饰学术研讨会”,研讨会由国博研究院、国博科研管理处和商务印书馆联合承办。会议邀请到馆内外二十余位专家学者分别就“问学之道——孙机先生学术追思”和“古代社会生活中的服饰”进行深入交流。会议首先邀请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张伟明、商务印书馆党委书记、执行董事顾青、孙机先生夫人李兰伟分别致辞发言,共同为孙机先生新书《孙机文集》首发揭幕。随后,七位学者分别就与孙机先生的学术交往,孙机先生的学术影响力、治学方法,以及《孙机文集》的编校经过等内容发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国博研究院古代舆服研究所所长扬之水担任以上环节学术总结。之后,十三位学者分别从特定服饰及其文化历史内涵、古代服饰名物考辨、服饰与清代民族交流融合,以及服饰文物的研究转化应用等四个角度入手,对相关服饰问题进行了阐述。会议最后,由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王方做学术总结。

(2023年9月26日)
9:00—9:10
开幕式(主持人:国博研究院院长、研究馆员陈煜)
与会嘉宾合影幕辞
9:10—11:50
第一议题: 问学之道——孙机先生学术追思会暨《孙机文集》新书发布
学术主持人:国博研究院院长、研究馆员陈煜
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研究馆员张伟明致辞
商务印书馆党委书记、执行董事顾青致辞
孙机先生夫人李兰伟发言
《孙机文集》新书揭幕仪式
袁 仄:《经师易求,人师难得 ——我的(M.PHIL. )论文与孙机先生》
葛承雍:《大先生:孙机先生的学术领航作用》
赵连赏:《高山仰止 景行于学——回忆孙机先生的教学事迹》
李 静:《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必读书——〈孙机文集〉》
霍宏伟:《致广大尽精微——孙机先生的学术境界》
朱万章:《艺术视野中的孙机先生》
赵 丰:《延续缘分,继承遗志,办好国博舆服研究所》
学术总结(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国博研究院古代舆服研究所所长扬之水)
13:00—14:55
第二议题:古代社会生活中的服饰(上半场)
学术主持人:北京服装学院教授蒋玉秋
黄梓桐:《加“襕”之袍与“襕衫” ——关于加“襕”之服形象的辨析》
崔晓旋:《宋代杂剧服饰的形成及风格类型考》
吴 比:《从“东坡巾”看服饰史中的文化交流》
苏文灏:《“假用”与“盛服”:明代庶人婚礼服饰考辨》
王业宏:《满族入关前的服饰刍议》
阮卫萍:《从清宫藏画析清代后妃衬衣考》
徐文跃:《衣冠异制,车书一家:清高宗不同族属妃嫔的冠服》
互动交流
15:05—16:45
第二议题 古代社会生活中的服饰(下半场)
学术主持人: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王方
景 闻:《乾隆时期宫廷绘画中出现民族服饰妃嫔成因浅析》
仇泰格:《好名泥古与指鹿为马——清代衣冠在满汉之间的改名与附会》
郭世娴:《试论清代皇帝服饰的视觉受众与皇权强化》
张 茹:《云锦色彩数字化研究与展示前沿研究》
秦 溢:《“众生百态”风俗画展中的古代百姓生活服饰解读》
朱亚光:《清代钿子的形成》
互动交流
16:45—17:00
学术总结及闭幕(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王方)

-
- 袁仄 北京服装学院
-
标题:《经师易求,人师难得 ——我的(M.PHIL. )论文与孙机先生》
摘要:
本文旨在讲述作者本人为撰写论文之故,拜见孙机先生及受教的经历。皆因孙机先生在学术上的悉心指导,使作者感受到孙机先生的卓越学术修养和优秀的学者风范。纪念文字通过讲述作者在孙机学术思想的启发、导引下完成M.PHIL.论文的经历中,感念孙先生学识领域的学术思想和学术高度。作者在先生的指导下选定论文选题,即研究唐代服装的“胡”化之实、之源、之由、之why……本文同时简单阐述作者论文的大致思路、框架等,既是向先生汇报,也是向与会同仁交流。这是一篇简朴的追思文章,旨在将个人步入服饰史论领域的经历及后来获得的些许学术成绩,以期纪念孙机先生,告慰孙机先生。
-
- 葛承雍 国家文物局文物出版社
-
标题:《大先生:孙机先生的学术领航作用》
摘要:
孙机先生是文物博物馆学界的一面旗帜,名符其实的“大先生”,多年来我们一直以孙先生为标杆,他以博大的胸怀和积极的实践走在考古文物研究的前沿,他的著作已经深入学界内外,不仅成为我们业内研究的案头书,也成为美术界、艺术界等其他学界吸取营养的必读书。
1979年他离开北大调入中国历史博物馆后,不仅是我国文博事业快速发展的见证者、参与者、推动者,而且在多个领域卓有成就,有着自己的治学独到领会,“大家底蕴,不忽精微。善于解剖,必有证据”。他既遵循传统,又不守旧于传统,讲究在符合历史规律的基础上进行开拓。不懂就是不懂,从不装懂。做学问的纯粹,使得他超脱于世俗之外。他说一位文过饰非的人,绝对不是真学者。他的思维不像一个90多岁的老人,更像一个英姿勃勃的年轻人。最敬佩的是孙机先生思维永远随着时代在递增,在前行,在探索,他所起的学术领航作用将在今后日显光芒,成为我们学术界永远怀念的“大先生”。
-
- 赵连赏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
-
标题:《高山仰止 景行于学——回忆孙机先生的教学事迹》
摘要:
2023年6月15日,著名物质文化史研究大家、中国国家博物馆终身研究馆员、我的忘年师友孙机先生逝世。今天国家博物馆举行先生逝世百日追思纪念会,回忆起曾经与先生接触的时光和他的治学风范,不由得感慨万千。
我与先生相识交往近三十年,以往除了时常向孙先生请教学习外,还有几个我们共同参与的项目或工作。即中国文联和文化部组织的“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指导和验收、“中国物质文化史料丛编”项目的编审,以及受聘于北京服装学院从事教学等。本次汇报主要向大家分享孙机先生在北京服装学院从事教学工作的部分事迹。
-
- 李静 商务印书馆
-
标题:《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必读书——〈孙机文集〉》
摘要:
《孙机文集》涉及中国古文物、古代物质文化的方方面面,学术论证丝丝入扣,是中国古文物研究、古代物质文化研究的重要工具书、案头书。文字表述简洁通俗,配有多幅作者亲笔手绘线描图,是学术文化普及的标杆读物。《孙机文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物质文化某些方面的系统论述;二是对某些问题的拨乱反正;三是对文物鉴定的案例及方法论;四是对文物的功能、应用及价值意义等的细致梳理;五是对文献整理的扎实贡献。
-
- 霍宏伟 国博研究院
-
标题:《致广大尽精微——孙机先生的学术境界》
摘要:
孙机先生驾鹤西归,令人怅然。综观孙先生的学术人生,一心向学,成就非凡。晚辈九年与贤为邻,十年共进午餐。耳濡目染,获益良多。今不揣浅陋,记录下向孙先生问学的收获,并努力将他的研究方法、学术特点、成功经验做一总结,以启迪后人,惠及来者。
孙先生不仅在做学问方面真正达到了“致广大,尽精微”的学术境界,而且还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人生理想境界:他不仅拥有生命的长度,智慧的高度,研究的广度,剖析的深度,更为重要的是,他还有着待人的温度。孙先生的学术人生,本身就是一部皇皇巨著。在未来的日子里,需要我们细细品读,意韵悠长。
-
- 朱万章 中国国家博物馆
-
标题:《艺术视野中的孙机先生》
摘要:
艺术视野中的孙机先生,在历史画与文人画的异同优劣、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艺术辨伪与治学方面表现出迥别于学界同仁的学识;在个案与考证研究方面亦与传统绘画史学不同。孙机先生亦是艺术实践的躬行者,长于临摹古画,绘制线图,笔力遒劲流畅,不输于专业画者。同时亦雅擅临池。他能写得一首好字,其小行书典雅、飘逸,富有学人气,而其隶书则雍容浑穆,得汉隶之遗韵。
-
- 赵丰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
-
标题:《延续缘分,继承遗志,办好国博舆服研究所》
摘要:
先生已逝,我们一方面怀念孙先生,追思孙先生,另一方面是学习孙先生,领会孙先生。但作为孙先生的受恩者、丝绸与服饰史领域的学者、以及中国国家博物馆舆服所的特聘研究员,更为重要的是继承孙先生的遗志,并结合《中国丝绸艺术大系》(国博卷)的具体工作,与国博同仁精诚合作,协力办好舆服研究所,做好中国古代丝绸与服饰文化遗产的保护、整理、研究、传承和弘扬工作。具体而言,或可以包括以下方面:全面整理国博丝绸与服饰收藏,制订纺织文物保护修复规划,推动丝绸与服饰文物的深入研究,不断改新和完善古代服饰史常设展览,持续办好一年一度的服饰论坛,共同培养丝绸服饰研究的后备人才,坚守沈从文和孙机先生创建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高地。
-
- 扬之水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
标题:第一议题学术总结
摘要:
关于孙机先生治学,专家们谈得很多,亦有不少生动例子,我们虽无法企及孙先生的生命长度、生命厚度以及天分,但先生的治学方法却是具体而能够践行的。其中最为首要的就是穷尽材料式的海量读书。做到这点,需带着思考来读书,既不盲从,更不迷信权威。所谓治学严谨、多闻阙疑,此为重要基础。师从孙机先生二十八载,让我牢牢记住的有如下三点:第一,何种文章可写,何种文章不可写?可写的标准是八个字“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反之则不能写。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前提是站在学术前沿;第二是治学的具体方法。首先是读书要做“长编”,这是做好学问第一步。在长编基础上找出最关键证据,用在最恰当之处,写出的考证文章才能言简意赅,崭截有力,足以服人。证据不足时,才需用穷举法;第三,写作证据不足时,绝不轻易动笔。所谓证据不足,分两种情况。通常思路对,材料会不断涌来,若非如此,即可能是思路问题。另一种情况则是思路正确,但证据链尚有缺环。针对这种情况,唯有耐心等待,待证据链齐全,再下笔行文。孙先生以他数十年的实践向我们昭示了他的治学路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和以此获得的硕果,而承载硕果的这一部《孙机文集》当是耸立在文物考古领域里的一座丰碑。
-
- 黄梓桐 北京城市学院
-
标题:《加“襕”之袍与“襕衫”——关于加“襕”之服形象的辨析》
摘要:
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因分裂造成的民族交流;引导社会生活方式发生重大改变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服装因各民族文化与风俗的融合与碰撞,呈现出与汉魏迥然不同的风貌,下摆附一条横襕的袍衫样式的出现便是其中一例。本文通过对加“襕”之服相关文献与形象史料的分析,发现中国古代服装史中加“襕”的服装包括加“襕”之袍与“襕衫”。加“襕”之袍的出现可以上溯至北周宇文护,后经过唐代长孙无忌提议,遂成为唐代官服的一种形制特征,影响到宋代至辽金时期的官服制度。襕衫的产生应该与唐代马周相关,自唐至明始终是士人之服,其形制特征与加“襕”之袍日渐分明。加“襕”之袍与“襕衫”二者在制度、功能、意义方面的表现并不相同,当今学者对襕袍起源之说难以分辨,应是与“襕”之袍与“襕衫”两者服装特征中因附会深衣而添加的横襕形制相似有关,初时“襕衫”与加“襕”之袍在形制上的差别尚不突显,随着历史的发展,二者在服装形制特征、功用方面的差异日益明晰,加“襕”之袍在礼制的品色制度中发挥效用;襕衫则成为后代儒生士人的代表符号。
-
- 崔晓旋 中国传媒大学
-
标题:《宋代杂剧服饰的形成及风格类型考》
摘要:
宋代杂剧服饰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它伴随着杂剧的发展及相近艺术群落的浸染,表现为一个漫长的继承、融合、转化过程。本研究将视阈扩展至宋代杂剧服饰所处的社会生态环境,在戏剧戏曲学、戏曲文物学的视阈下,系统地考察宋代杂剧服饰的历史生成语境和演化机理,依据宋代杂剧服饰遗存资料的性质和杂剧演出场合之别归纳服饰风格类型。可以说杂剧服饰是为宋代市民文化转型的侧影,一方面传学教坊杂剧部色演出规制,逐渐形成多层次、丰富性、带有平民情趣的装扮体系,一方面市民“俗”文化也对士大夫“雅”文化呈渗透之势,标志着宋代文化雅俗共赏的特征和大众化转向。
-
- 吴比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
标题:《从“东坡巾”看服饰史中的文化交流》
摘要:
帽在中国的历史非常悠久,但最早为北方少数民族所喜戴。在汉代及以前的首服体系中,中原地区的主流语境往往崇尚冠而轻视帽。但经历过魏晋风度和南北朝民族大融合的洗礼后,士人们反而开始以戴帽为雅,乃至于参与帽的设计与改造。唐及五代,有檐有棱的“乌纱帽”已流行于士人群体,频繁出现在诗文中。北宋以降,乌纱帽出现了诸多名目,虽整体造型一致,但方圆高低的细节各有不同,其中有一种身高檐短、上宽下窄的方帽尤其受到苏轼喜爱。由于苏轼巨大的影响力,这种方帽在宋代和明代分别有了“子瞻样”和“东坡巾”的专名,后又被民间附会为苏轼发明。明清时,东坡巾已成为苏轼画像中的程式化符号之一,并传播到了越南、日本、朝鲜等东亚文化圈的国家。梳理东坡巾的演变过程,可使我们从文化交流融合的角度更好地感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特殊性。
-
- 苏文灏 中国传媒大学
-
标题:《“假用”与“盛服”:明代庶人婚礼服饰考辨》
摘要:
今人常视明代婚礼冠服为中国婚俗文化衣饰用度之大成,女子的凤冠霞帔、男子的乌纱帽与圆领袍被认为明代男女成婚之日的标准礼服。然而,回阅明时有关庶人婚礼服饰穿用要求之记载,则与后世共识颇有差异。品官子孙“假用”九品服,百姓子弟仅可着皂衫、折上巾,而新婚女子冠服只用“盛服”明示,无详细名目。如上服饰制度书写似乎与所谓明代婚礼冠服标准相去甚远,典籍所载与多数学者所持明代庶民婚礼服饰研究推论产生了“史实”与“史识”的对撞。厘清明代庶人婚礼服饰客观样貌,需从“假用”与“盛服”入手,辨析已有学者论断,关联历史维度、服饰制度、社会文化及婚俗传统,以图像、文本、实物结合作研析方式,还原明代庶人婚礼服饰真实样态。
-
- 王业宏 温州大学
-
标题:《满族入关前的服饰刍议》
摘要:
根据《满洲实录》的插图和清初史料,满族入关前的服装(衣服)可大至分为朝衣、袍、褂、甲、袄和其他等几类。
朝衣是最重要的服装,文献中与朝衣相关的称谓还有朝服,披肩,披领、扇肩等,披领是朝衣的重要特征。插图中有披领的衣服有四种样式。穿披领服饰的人物为努尔哈齐,女真侍卫,蒙古将领,身份不明的蒙古人,都出现在比较重要的场合。插图中有披领的服装与入关后满族的朝衣款式不同。朝衣的披领,可溯源至辽金时期。
袍是满洲从上至下穿着最为普遍的服装,插图中的袍分有无马蹄袖和有无补子,共四类。袍的称谓从文献记载看是皇太极之后才普遍使用,努尔哈齐时期统称为衣服。有补的袍服均有马蹄袖,圆补为努尔哈齐所穿,方补为部将所穿。图像中袍的款式与入关后高度相似,只存在几处结构的差别。
褂也是入关前的重要服饰,《满洲实录》中褂的形制有五种,史料记载的褂有:长褂、马褂、短褂、齐肩短马褂、齐肩无袖短褂、齐肩短褂、女褂、女朝褂、女长褂、皮端罩、短皮端罩、长皮端罩等,图像中的五种包含在这其中。
甲,是图像中出现频率较高的服装,有二十多种样式。史料记载有“甲,短甲,绵甲,盔甲,铁甲,甲胄,明甲,藤皮甲,纸甲”等。其基本形式为上下分开的甲衣和甲裳,可以分开单独穿。这些样式在入关以后大部分继续使用,但是可能调整了使用者身份。
袄等其他服装在入关后仍然广泛使用,一直延续到近现代。
努尔哈齐建立后金政权后,进行了服饰制度的草创,效仿明朝确立官员补服和冠顶制度,而对于衣服,努尔哈齐只要求根据面料的优劣进行等级划分,从文献上看,蟒缎是这一时期的重要衣料。天聪时期,皇太极进一步制定服饰制度,规定了正式场合穿朝衣,平时穿袍。规定黄色、龙纹为大汗专属纹样。朝衣和袍基本依旧根据面料的优劣划分等级,蟒缎的纹样较以前有所增加。崇德时期,皇太极称帝,服饰制度中增加了冠顶,翎、带等配饰和坐褥的使用规则。强调“依我朝之旧不敢改焉”,所以服装仍延续天聪时期的制度,蟒缎的纹样更加丰富。入关后,服装制度的不断修订,直到乾隆时期臻于完善。在这过程中,服装出现了分类,有了色彩、纹样、配饰等方面的详细使用规则,蟒缎一词也随着这些规则的出现,逐渐不被提及。
从皇太极训诫“后世子孙勿轻变弃祖制”到乾隆皇帝钦定《皇朝礼器图式》“礼不忘其本也,润色章身,取其文,不必仅沿其式”,清代统治者一直遵循“未可轻革旧俗,永守勿愆”。永守勿愆的是满族入关前的服饰形态,润色章身是清代服饰制度不断修订的重要内容,从入关前蟒缎的分类使用开始,到礼、吉服等服饰的分类,最终完备。
-
- 阮卫萍 故宫博物院
-
标题:《从清宫藏画析清代后妃衬衣考》
摘要:
清代后妃在大典、祭祀和一般礼仪、喜庆等日子要穿礼服和吉服,这些服装都有明确的典制规范,而她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穿的服装则称之为便服,在典制中少有明确的记载。故宫藏清代帝后画像中,皇后像大多是穿礼服和吉服,但清道光皇后像中有四幅生活像,《清孝慎成皇后观竹图》《清孝慎成皇后观莲图》《清孝全成皇后便装像》《清孝静成皇后便装像》和清文宗咸丰皇后二幅《清孝贞显皇后便服像》,这几幅绘画作品是皇后真实生活写照,皇后在图中身穿大襟右衽、宽大挽袖、直身花卉长服,或梳两把头戴花,或戴大拉翅,系领巾,几幅图中皇后所穿长服的形式,从直观上看,都似本文中要谈及的衬衣。
衬衣是便服中一种,从字面上理解,衬衣是穿在外衣里面的内衣,而清代后妃衬衣则有其特殊性。其基本形式为圆领、大襟右衽、直身不开裾式长衣。本文试从什么是清代后妃衬衣、后妃衬衣的特点、时代特征、何时穿用及清代后妃衬衣在定名中存在的问题等方面做了全新的考证,从而使人们对清代后妃衬衣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
-
- 徐文跃 自由学者
-
标题:《衣冠异制,车书一家:清高宗不同族属妃嫔的冠服》
摘要:
乾隆之世,经由清高宗的十全武功,众多疆域纳入清朝版图,诸多部族归于清朝治下。高宗分属不同部族的妃嫔,亦在此疆域、族群的渐次整合过程中被收入后宫,生动反映了清朝对统合不同疆域、族群所作的努力及“天下一家”的理念。本文聚焦其中的一个侧面,即高宗不同族属妃嫔的本族冠服,对相关图像资料、档案文献、传世实物作了梳理、考察。同时,对清代宫中所用冠服的实态亦有揭示。
-
- 景闻 故宫博物院
-
标题:《乾隆时期宫廷绘画中出现民族服饰妃嫔成因浅析》
摘要:
随着档案的公开、文物影像的公布,档案和绘画向我们展示了皇帝内廷女性民族构成的多样性。乾隆皇帝执政时期,绘制了大量具有纪实性的宫廷绘画,在这些宫廷绘画中除了皇帝本人,还包括有乾隆皇帝的后宫妃嫔们。目前公开的故宫博物院藏乾隆时期宫廷绘画《清人万国来朝图轴》、《清人画弘历塞宴四事横轴(掼跤)》、《清人画崇庆皇太后八旬万寿图贴落》三幅绘画,出现有满、蒙、回、汉多民族的妃嫔形象。本文结合文献资料,对绘画中后妃的身份进行分析,并对画作缘何出现民族服饰后妃的成因做出浅析。
三幅画作都曾是乾隆时期重要宫殿使用的贴落,在反映重大政治事件具有纪实性质的贴落上绘制穿着满、蒙、回、汉等民族服饰的宫廷妃嫔形象。结合三幅画作绘制的时间,以及外藩蒙古和回部妃嫔进入宫廷的时间,均在乾隆重要的平定准葛尔部和平定回部战争之后,是皇帝民族联姻政策的一部分。后宫女性民族来源的多样性,正是皇帝统御四海的体现。事实上,不仅绘画中体现了乾隆时期后宫穿着本民族服饰的史实,文献档案也说明,在清代顺治、康熙、雍正、乾隆朝,都不同程度存在着汉、蒙、回等民族的妃嫔身影,宫廷中存在着民族服饰的制作和穿用情况。她们被允许穿着本民族的服饰在宫廷中生活,真实宫廷服饰的复杂性远超我们惯常的理解。
-
- 仇泰格 故宫博物院
-
标题:《好名泥古与指鹿为马——清代衣冠在满汉之间的改名与附会》
摘要:
清代帝王在衣冠配饰方面,始终强调保持自己本民族的特征,宣称汉人衣装必定会导致骑射等本领废弛、抛弃满洲旧俗,并高调拒绝采用汉人服饰,希望子孙在穿着上沿袭本民族旧制,勤习骑射,拒绝汉俗。另一方面,在满洲统治者眼中,北魏等之前入主中原的异族王朝的衣冠策略,则是负面典型,他们被认为因完全接受汉人衣冠样式,放弃本民族旧俗而招致了国家败亡。虽然如此,乾隆帝在修订礼制时,将自己满洲民族衣冠配饰元素的汉文名称进行了重新改换,新改订的名字大多出自儒家经典及前朝典制中的汉民族古代衣装,如此以附会古礼、前朝典制对满洲本民族服饰加以文饰,以使之显得合乎中原古制,增加其体面性与正统性,减少其异族色彩。本文将从满文文献出发,考证满洲服装中三处元素(带饰活计、冠顶提系、袍服细褶)的源起和本来用途,以及这些服装元素在乾隆帝修订礼制的时候,是如何被重新命名附会前代汉民族衣冠的。从这一考察过程中,可以看出异族在入主中原之后,在冠服政策上的第三条折衷策略:既不似北魏王朝全盘无保留接受汉族衣装,也不真正如某些清代皇帝对外宣扬的那样,严拒汉人衣冠制度,恪守本民族旧制,而是在大体不改变本民族服饰形制样貌的前提下,将本民族服装元素改用儒家经典、前朝旧制中的古名,附会中原汉人古代衣装,以减少本朝衣冠制度的异族色彩,增添其正统性。
-
- 郭世娴 中国国家博物馆
-
标题:《试论清代皇帝服饰的视觉受众与皇权强化》
摘要:
古代服饰的政治功能通过观看这一社会活动具体实现。皇帝服饰是服饰具有政治功能的典型代表,本文以对清代皇帝服饰的观看活动为例,探察古代服饰实现政治功能的具体过程。
-
- 张茹 肖妍娜 南京博物院 南京江南丝绸文化博物馆
-
标题:《云锦色彩数字化研究与展示前沿研究》
摘要:
云锦是中国传统纺织技艺最高水平的代表,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的人类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被以《红楼梦》为代表的多少小说或古代技艺相关文献所记载。以往关于云锦传统工艺的研究基本是以纺织史、设计学角度做定性研究为主,近些年云锦工艺研究逐渐开始尝试从人文艺术与科技交叉融合的全新视角进行定量研究。就某一专题进行数据采集和分析,从微观深入挖掘云锦技艺和文化背后的信息,成为非遗数字化理论发展到现阶段最前沿的一种数字化研究方式。本报告以江南丝绸文化博物馆一项云锦色彩数字化研究与展示项目为案例,从云锦色彩古籍文献信息量化研究为起点、又分别从云锦染色流程规范、云锦染色实践过程量化操作,以及常用云锦色数字化研究这几个方面,总结了云锦数字化前沿的研究方法和展示方式,也为纺织非遗数字化研究提供直观、可借鉴的操作指南,具有实践指导意义。
-
- 秦溢 中国国家博物馆
-
标题:《“众生百态”风俗画展中的古代百姓生活服饰解读》
摘要:
古代百姓生活服饰是其欣赏生命、尊重自然、日用即道的内心生活与审美人格直观体现。“众生百态——故宫博物院藏历代人物画特展(第三期)”中,部分风俗画以“刻实”的笔墨形式,为我们提供了观看古代百姓服饰“史”的资料。从绘画中选取宋元时期乡村底层人民服饰,宋代孩童服饰和清前期村市手艺人服饰,结合历史背景和绘画语境,辨析这一时期服饰的特点,还原服饰的真实,解读绘画中服饰正确的观看方式。
-
- 朱亚光 中国国家博物馆
-
标题:《清代钿子的形成》
摘要:
清代钿子是满洲贵族妇女特有首服类型之一,在造型与佩戴方式上区别于同时期汉族女性首饰。钿子的产生与满洲先祖女真妇女发型发饰、清代满洲妇女旗髻造型以及清代统治政策等因素有关。其原型和基础是金代女真贵妇"辫发盘髻"上所加之"裹巾"。钿子伴随满族妇女旗髻功能变化形成,而清代统治者对遵循满洲服饰传统的强调则是钿子在造型始终保持民族特色的主要原因。
-
- 王方 中国国家博物馆
-
标题:会议学术总结
摘要:
生活服饰与人类日常生活的联系更加密切,更能深刻地反映出古代社会的各个层面,可谓包罗万象。学者们的研究内容和视角丰富,所探讨的问题,业已超出对服饰本身的关注,在服饰研究基础上更加注重其背后所蕴含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问题,研究视野开阔新颖。此外,本次服饰研讨会还很好地体现出“研、学、用三位一体” 的现代服饰研究特点:充分利用研究成果,融入现代化高新技术,进行更加生动、更为形象的数字化展示。之后她谈到,作为服饰研究学人,对孙机先生的深切缅怀,莫过于以先生的治学精神来启迪后人、惠及来者。本次研讨会迎来很多新面孔,恰能说明古代服饰研究领域后继有人、充满朝气。希望大家能沿着孙机先生的治学道路不断深耕,在古代服饰研究领域取得更加扎实、更为丰富的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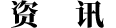
-
- 国博举办“孙机先生学术追思会暨第五届中国古代服饰学术研讨会”2023/09/27
-
- 孙机先生学术追思会暨《孙机文集》新书发布会在国博举办2023/09/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