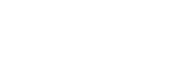10月27日,中国国家博物馆召开“佛教造像的中国文化内涵学术研讨会”。本次会议由国博研究院主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央美术学院、上海博物馆等单位的近30位专家、学者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参加了论坛。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丁鹏勃出席并致开幕词,国博研究院院长陈煜主持研讨会开幕式。
研讨会分主旨演讲和分论坛四场进行。主旨演讲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魏道儒,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金申,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李静杰分享了近年来关于佛教造像的研究成果,就“隋唐五代宗教态势与思想发展”“新发现的十六国时期法常造金铜佛立像”“汉文化地区佛教造像的发展格局”进行了研讨,在观点、思路、视角等方面均有诸多创新。

研讨会的第一个议题是佛教中国化相关问题研究。与会学者提出,佛教融入中华文化基因,与佛教中国化是分不开的。佛教中国化是佛教适应中国社会的过程。佛教造像西来以后,顺势发展成为符合中国本土文化的艺术形式,在历史上发挥着和合共生、交融互补的作用。
第二个议题是从佛教史、佛经角度讨论造像的中国文化内涵。学者们分别介绍了北京房山云居寺的重要影响、唐宋佛教造像观念的变化以及元明清佛教造像的繁荣与衰退过程等研究。
第三个研讨的议题是从佛像图式讨论造像的中国文化内涵。学者们从不同学科角度分析了和田博物馆藏青铜座佛像、大足牧牛石刻、西安出土史君石堂等图像,也有不少学者就云冈、龙门、敦煌等石窟发表独到见解。此外,国博学者运用新的研究手段,介绍了国博收藏布袋和尚造像、宋明木雕造像,复原木雕造像工艺,对其来源进行研究。
同时,与会专家对古代佛教造像的保护和利用提出了建议,为国博馆藏佛教造像的展陈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学术支撑,对推进中国佛教造像学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有着重要意义。
附录:
论坛发言摘要
主旨演讲
隋唐五代宗教态势与思想发展
魏道儒(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从隋朝建立到安史之乱,所有宗教都经历了自己在隋唐五代发展演进的黄金期;从安史之乱到北宋建立,六种宗教或者趋于衰落,或者潜行民间,或者完全灭绝,或者在义学落寞中开启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修行方式、传教方式的转型。隋唐五代形成的儒释道三教平等并立、并盛、并行的新态势,历经整个封建社会而没有本质变化,并且持续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发挥作用。围绕生命超越和伦理教化两个支点展开的道教思想蓬勃发展,优秀学者层出不穷,重要著作持续涌现,创新学说丰富多彩。发展势头最为强劲的佛教,主要成就表现在国际文化交流扩大、理论创新内容鸿富、融入中华文化基因、藏传佛教勃然兴起四个方面。
新发现的十六国时期法常造金铜佛立像
金 申(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
僧法常造释迦牟尼佛立像出自河北省中部一带,像背后有阴线竖刻“石赵法常佛”5字,其中“石赵”应指石勒、石虎所建的后赵,“法常”或为《高僧传》“佛图澄传”中所记佛图澄之弟子法常。带铭文的十六国后赵时代的金铜佛像传世甚稀,此造像标明为后赵时代,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汉文化地区佛教造像的发展格局
李静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中国佛教造像可以粗略划分为汉地、西域、藏地三个部分,汉地佛教造像体现了汉民族思想观念,西域、藏地佛教造像带有当地文化和民族特质,都是中国化或中国文化内涵的佛教造像。
汉末三国两晋时期,佛教造像在中原北方、四川、长江中下游地区有所流行,但规模十分有限。南北朝、隋代佛教造像呈现一体化发展态势,广泛分布在中原北方、长江流域以及河西走廊,从交通、经济、文化发达区域,普及到僻野乡村。造像规模在南北朝前期还比较有限,南北朝后期、隋代空前大发展,促成汉地佛教造像发展第一次高潮。唐宋时期佛教造像呈现一体化发展脉络,发展节奏又可以分为唐五代、宋辽金两个阶段。元明清时期佛教造像,在延续、衰退过程中发展,于明代呈现一度繁盛,又清新悦目的新气象。学界以往关于汉地明代佛教造像的认知,多局限在水陆画方面,近年来通过陕北明代石窟、四川明代摩崖造像,以及地面寺院之考察,得知明代造像反映成就法身、往生净土、救济众生思想依然发达。而且,在人物造型、图像设计等方面取得新成就。
第一场讨论
云冈石刻博山炉形象的渊源
练春海(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
云冈石窟中有大量表现的博山炉图像,这些图像与汉朝发明的博山炉有渊源关系,但是汉朝与云冈造像时期存在一定的时空距离,这种形象的传播依靠的是地缘与工匠流动因素。魏晋时期对博山炉使用的管控有所变化,汉以后的博山炉在上层社会中的象征意义削弱,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转化为一种纯粹的符号,并因此进入佛教文化系统。
洞中藏宝:房山佛教的历史文化
张雪松(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北京房山自汉初隶属于古代涿郡,六世纪上半叶北魏时期佛教传入房山,开始建寺安僧。一千多年以来,云居寺、石经山、天开寺、上方山等房山佛教名胜的历史文化绵延不绝,在中国北方,乃至整个汉传佛教文化圈内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从法身到肉身——初唐佛像样式转变的观念背景试论
吴 虹(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艺术哲学系讲师)
佛教艺术风格的发展并非仅仅是不同审美意识或地域文化交流的结果。作为崇拜的对象,佛像的造型必然还包含、反映着民众对于佛的概念和性格的认识。研究从佛像观念的角度重新审视初唐佛像样式的转变,认为7世纪末,民众对于佛像的观念发生了重要变化,从南北朝时期被认为是“法身”的应化,到此时变化为“肉身”的佛像。初唐风格的确立和流行,或许可以在这样的观念背景下进一步分析和思考。
戒与礼的冲突与融合
夏德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
戒律是佛教徒的基本行为规范,体现着佛教的基本精神。戒律一传入中国,就与中国传统的礼文化产生了激烈冲突。在区分戒与礼异同的基础上,求同存异,实现“道并行而不悖”,成为佛教徒努力的方向。本文将从“义”和“制”两个层面分析戒与礼各自的内容、性质,梳理戒与礼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从冲突斗争走向融和并存的主要发展阶段,考察戒与礼在互相影响下的双向扩充,在一个特定方面展现佛教中国化的曲折历程。
大足石刻禅宗造像管窥
杨 浩(北京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副研究员)
大足石刻中宝顶山石刻有一组禅宗牧牛图的刻石,在石刻艺术中仅此一见。该组刻石是对北宋杨次公(杨杰)《证道牧牛颂》的生动再现。受廓庵禅师《十牛图》影响,人们常以为宝顶山牧牛图亦为十组图。根据目前残存的颂词判断,当为十二组图。与廓庵《十牛图颂》相比,杨杰《证道牧牛颂》牧牛过程更为细腻,但宗趣则是相同的。
隋唐洛阳城与龙门石窟空间关系之辩证
霍宏伟(国博研究院副院长)
隋唐洛阳城是中国古代城市史上的一座重要都城,龙门石窟则是我国三大佛教石窟之一,今重点关注的是两者的空间关系问题。自隋至唐,龙门实现了从洛阳城中轴线南端基点到佛教圣地的进一步转变。城与窟的基本关系,可以归纳为“城兴窟盛,城衰窟微”。以龙门石窟现存的造像题记作为切入点,细致梳理与洛阳城行政区划相关资料,涉及洛州、河南县及洛阳县,城内建置类型分为里坊、市场及寺院。将龙门造像题记结合历史文献进行分析,从而构筑起等级森严的洛阳城社会空间。在都城研究整体观的视野下,来重新审视隋唐洛阳城与龙门石窟的空间关系,可以概括为“北南呼应,城窟一体”。
第二场讨论
和田博物馆藏克什米尔风格造像及相关问题
陈粟裕(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
和田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克什米尔风格青铜坐佛像,为策勒县老达玛沟一带的征集品。像座下方有梵文榜题,经研究可知此造像为吉尔吉特一带的一位军事指挥官全家供养之物,年代约为6至8世纪之间。此期,吉尔吉特周边为Patola Shahis王朝(小勃律)所统治,佛教繁盛,并且金铜造像工艺高超。和田博物馆的这件青铜坐佛像真实反映了于阗与小勃律在宗教艺术领域的交往。另外,根据对阿里地区后弘期初期佛教雕塑的考察,可知Patola Shahis王朝的金铜造像所秉承的克什米尔风格,对古格王朝初期的佛教造像予以深入影响,成为后弘期初期佛教艺术在藏地复兴的重要来源。
北周史君石堂与北朝佛塔艺术
徐 津(国博访问学者)
在过去几十年发现的北朝入华粟特人石葬具中,西安出土的史君石堂(580年)是最受关注的一件。该石堂图像雕刻精美,内容丰富,是中古美术乃至丝绸之路艺术的一件代表作。自2003年该葬具出土以来,学者们对它的研究大都集中在墓主的祆教信仰上, 石堂图像也多被看作是祆教或是琐罗亚斯德教教义的图示。研究从佛教艺术的视角重新审视史君石堂,提出石堂的营造受到佛塔艺术和图像的影响。石堂和佛塔的结合,体现了北朝隋唐时期儒家礼仪和佛教传统融合的时代趋势。
累世装銮:MFA藏水月观音像的年代学和色彩叠压现象
张建宇(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
波士顿美术博物馆藏一尊木雕水月观音像(入藏号20.590),来自山西稷山。1920年该像入藏时呈灰白色,1956年清洗掉表面色层,呈现出如今的面貌。2014-2016年,策展人白铃安(Nancy Berliner)和修复师Abigail Hykin女士对该像进行科技检测和修复,发现更多发愿文字,笔者初步判断为金大定十九年(1179)所造。通过检测,基本弄清这尊木雕造像的材质、制作和修复过程,以及“累世装銮”现象。造像服饰部分(特别是红色长裙)保留了金代色彩和截金工艺,而最初的肤色则被明代金色装銮所覆盖。
石家庄毗卢寺释迦殿壁画相关问题述说
伍小劼(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石家庄毗卢寺主殿毗卢寺的壁画水陆会保存好,艺术水平高,受到世人关注。前殿释迦殿壁画保存情况不佳,则少受人关注。释迦殿绘制的为佛本生故事,通过明嘉靖十四年(1535)的《重修毗卢禅寺碑记》可知,前殿(释迦殿)绘有“壁画十地”。有学者提出“壁画十地”的底本为《释迦如来十地修行记》,壁画中的“金牛太子故事”等能与《释迦如来十地修行记》相应,但也有不相符的地方。这一意见值得重视。笔者也提供了一种新的《释迦如来十地修行记》文本。
丝绸之路视角下佛陀造像源头探析:古希腊罗马文明中的印迹
翁淮南(中国国家博物馆图书资料部主任)
佛教产生后的五六百年传播是缓慢的,但到公元2世纪,佛教和以佛陀造像为核心内容的佛造像艺术却迅速在中国发展并繁荣起来。其中的关键,是有了“复杂”物质与文化需求催生的“复杂”丝绸之路。特别是佛跟城市商业和富裕阶层的结合,促进了佛教和佛造像艺术的发展。因为中国和丝绸之路,佛教从一个地方性信仰发展成为世界宗教。梳理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1世纪前后古希腊罗马文明的雕塑,在服饰、发型、耳朵、眼睛和卧姿等方面,均能发现呈现佛陀造像艺术源头的元素。佛陀造像在中国的传播,不是简单的线性传播。在古希腊罗马文明中对佛祖造像溯源,为开展“一带一路”视野下佛造像中国化及海外传播研究,提供另一种思路。
《佛说般舟三昧经》中的三世佛金身及造像思想研究
马宗洁(国博研究院副研究馆员)
史载东汉支娄迦谶翻译的《佛说般舟三昧经》中有三世佛金身及造像思想的教义内容,阐明身黄金色是三世佛的共性特征,倡导信众常造佛像,揭示过去佛造像(以私诃摩提佛造像和萨遮那摩佛造像为代表)、现在佛造像(以释迦牟尼佛造像、西方阿弥陀佛等十方佛造像为代表)和当来佛造像(以善觉佛造像为代表)均应具有金身,佛像金身并非佛造像中的个例,而应是佛造像中较为普遍的现象,为多种题材的佛像金身提供“通用”的教义理论阐释,对于佛像金身研究和展览策划有重要意义。
第三场讨论
中国的末法思想与邺下刻经流布
何利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副研究员)
佛法住世可分为正法、像法及末法三个阶段。中国末法观念始兴于公元四世纪的东晋十六国时期,六世纪以后广为流行,并由此出现了大量的佛教刻经,形成了以邺城为中心的河北地区和以泰山为中心的山东地区两大刻经密集分布区域。
作为十六国以来北方佛学重镇,邺城佛教在东魏北齐时期(534-577年)取代洛阳成为中原北方地区的佛教文化中心,并在公元六世纪中期达到极盛。史载“属高齐之盛,佛教中兴。都下大寺,略计四千。见住僧尼,仅将八万。讲席相距,二百有余。在众常听,出过一万。故宇内英杰,咸归厥邦。”值得注意的是,在邺城附近的许多石窟及摩崖上都刊刻有佛教经文,比较集中的地点有河北邯郸南北响堂山石窟、涉县娲皇宫石窟、河南安阳小南海石窟、灵泉寺石窟、卫辉香泉寺石窟等。与邺城刻经关系密切或时代略晚的还有河北曲阳八会寺和河南林州洪谷寺刻经,另外还有少量的刻经碑流传下来。邺城地区北朝晚期义学发达,各种学派的思想在此融汇,刻经内容也极为丰富。山东与河北地区的刻经虽然在形式上有一定的差异,由于两地间交流的频繁,其本质上存在诸多内在的联系。北朝晚期的刻经在形式和功能上不仅继承了早前彰显、诵读、禅观乃至修积功德等目的,更结合了当时的历史和宗教背景,赋予了刻经以护持佛法、保存经像、以备法灭的重要内涵。这一功能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宗教思想,并在实物证据上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概括而言,中国的末法观念于十六国时期的河西地区初露端倪,并波及世俗信众,北凉石塔上即已发现与末法相关的题铭和最早的石刻佛经;北朝晚期末法思想泛滥,为使佛法不灭、经典长存,石窟和摩崖刻经在中原北方地区极度盛行,并在北齐境内形成了邺下和泰山两大中心;邺下僧人及北齐刻经对北京房山云居寺刻经、陕西金川湾三阶教刻经及四川地区唐代刻经的出现产生了直接且深远的影响。
三重秩序:以莫428窟空间语义为例
郑 弌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从不同学科视野出发,石窟内在的空间秩序其实可分为三个层面:石窟考古学视野下的空间形制、石窟美术史视野下的图像程序,以及时常被忽略的仪式时间。相对于构建石窟空间内部主体的图像程序,仪式时间通常被视为世俗且外部性的,大多跟供养人的进香、祭祀或供奉行为密切相关。而造像题材的时间性,往往被化约为单一题材内部的叙事时间,而忽略了贯穿于大多数佛教造像内部的仪式时间,前者范围内典型例子如北朝长卷式或多组式经变(微妙比丘尼因缘品等),又如晚唐牢度叉斗圣变与维摩变等。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观照的缺席或化约,容易让研究者忽略了隐含在图像内部更丰富的维度,亦使图像程序的诠释局限于相对的静态。
莫428窟图像构成繁复,其中心塔柱四相成道、涅槃图、所谓“金刚宝座/五分法身塔”等题材多有争议,既反映了北朝晚期敦煌造像观念来源于区域间的互动,其图像秩序亦表明其观念层次的多义性。作为莫高窟北朝最后阶段,即北周时期代表性洞窟,围绕莫428窟所展开的相关学术问题,历来是敦煌考古学、美术史乃至社会史研究的重点与难点。其中,关于该窟西壁“金刚宝座塔”的方位、定名、释义,自宿白、施萍婷等诸位先贤以降,从各自学科立场和所据材料,多有讨论,相继提出了“金刚宝座塔”“五分法身”等论说;然学界迄今并未就此图像达成共识。借助于近年来北朝佛教史、佛教考古与佛教美术整体研究的推进,有可能将该图像置于更广阔的视野,尤其是北朝晚期佛教义学、法华思想对同期佛教图像的影响与互动。
回到428窟内各图像配置,正如上引诸前贤观点,窟内以千佛、卢舍那法界像、释迦多宝并坐像等图像或体现了法华与华严交融之下的禅观主题。然而,此种禅观的主体是谁,其具体的仪式时间如何在诸种图像间展开?本题拟就此角度加以探讨。此外,莫428窟西壁图像分布既上下分层,亦南北分栏,规制繁复。五分法身塔不仅在该壁面占据较为核心的位置,与同壁面涅槃等图像有着密切的观念性联系,其与全窟空间布局及卢舍那法界像等亦有着整体性的图像秩序。莫428窟的空间语义与造窟思想,正蕴含其间。
布袋和尚经典与图像的流变—以国博馆藏为例
张 萌(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品保管部研究馆员)
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布袋和尚造型的金铜造像共有187件,全为明清时期造像,其中有1件伴虎神僧组像,有10件按照其图像特征判断为藏传佛教造像,为藏式十八罗汉中的哈香尊者。
研究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梳理相关佛典记载,解析变化原因。五代时期出现的布袋和尚信仰,相关生平记载自北宋初年见于佛教典籍,并逐渐丰满,细节越来越详尽,神异成分逐步添加,到元代达到顶峰,但是在明代发生了转折,退回南宋时期的记述范畴,这种发展轨迹背后有深刻的社会因素。第二部分梳理布袋和尚图像的发展史,虽然文献记载布袋和尚的图像出现在五代时期,但现今可以看到最早的此类图像是北宋时期的,南宋时期是布袋和尚图像发展的繁荣期,实现了部分元素的重大变化;元代,正坐式布袋图像逐渐取代倚坐式,布袋和尚图像基本定型;明代,统治阶层在抑制弥勒教的同时有意提高布袋弥勒的地位,布袋和尚正式取代弥勒佛的地位,尊格得到提升。第三部分梳理布袋和尚形象的转用现象,由于布袋和尚是中国佛教艺术中流行的题材之一,所以很快便出现了图像转移或母体借用。布袋和尚图像出现之初,布袋罗汉图像也出现了;14世纪,作为哈香尊者进入藏传佛教神系中。明代,出现伴虎的布袋图像,这是将布袋和另一位禅宗散圣丰干的形象混用。
艺术技术史视野下的国博木雕佛造像调查
孙 博(中国国家博物馆陈列工作部副研究馆员)
国博佛造像展和古代中国基本陈列共展出宋明之间木雕佛造像7件,代表了近世汉传佛教寺院木雕造像的艺术成就。由于过去风格学、类型学、图像学等研究方法的局限,对于这批脱离寺院原位,造像题材较为普通的佛雕,专门讨论的学术成果极少。有鉴于此,申请了“国博馆藏宋金元木雕佛造像制作工艺的研究”课题,从艺术技术史视角复原这批造像的工艺,增进对晚期汉传佛教木雕像的认识。木雕佛造像调查是课题组对国博馆藏明代水月观音木雕像的初步调查成果,发现此作存在不同时期彩粧工艺叠压的现象。底层,即初始彩粧中采用了拨金、截金等奢华工艺,猜测其原出明代宦官家庙。
上海博物馆藏云冈石窟造像整理
师若予(上海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上海博物馆收藏有一批云冈石窟造像。这批造像是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组织考察队于1940年在昙曜五窟内、外平整地面时所采集众多造像中的一部分。特别珍贵的是上博收藏的这批造像多数收录于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编著的《云冈石窟》第十四卷图录中。水野等人于日本战败前将他们在云冈石窟采集的部分造像,以及万安北沙城、阳高古城堡汉墓出土的部分文物带回日本,藏于东方文化研究所中。抗战胜利后,这批文物中的一部分经李济先生等人的努力于1948年被成功追索回国,并于1955年入藏上海博物馆。
圣僧的生活——僧堂置像与寺院的日常
王大伟(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自魏晋始,寺院的僧堂或食堂中就开始置圣僧像,禅宗更是将圣僧位设定为僧众生活的固定龛位置于生活空间中。圣僧作为一个象征,曾有僑陈如、宾头卢、文殊等多种形象的演变,虽代表性有所差别,但基本都围绕僧众的日常与修行生活树立了他们的神圣意义。圣僧依然要“生活”,所以圣僧侍者成为保证圣僧生活的关键人物,这也成为寺院中很别样的生活样态。
关中地区佛道造像碑新探
蔡晓菁(国博研究院馆员)
关中地区发现有为数不少的北朝至隋代佛道造像碑,这些造像碑同时塑造佛教和道教的最高信仰对象,也被称为佛道混合造像碑、双教造像碑等。以往研究没有注意到像碑的佛道二教内容并不平衡,过于强调佛道交融的一面,也忽略了佛道造像碑出现的地域性特点。佛道造像碑与宗教的区域性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供养者的身份多样,造像的目的不同,主导者的信仰有别,致使所造佛道造像碑在布局与愿文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偏向,并非都是对佛教、道教的共同崇拜。同时,“化胡说”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佛道像碑的出现与当时朝堂之上发生的二教论争并不矛盾,像碑在民间的实际功用淡化了它对佛道竞争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