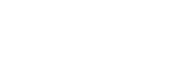【内容提要【1933年1月日军进攻山海关,席卷热河,威胁平津,华北地区告急。黄郛被忙于“剿共”计划的蒋介石推到解决华北危局的前台,主持《塘沽协定》的签订、大连—北平善后会谈、关内外通车通邮谈判等工作。其忠诚谋国之苦心孤诣并不为众人所褒扬,在当时被主流舆情称为卖国贼和投降路线的代表人物,似乎至今也难被谅解。本文旨在进一步探讨这段历史,既正视他竭力维护国家民族利益,不甘投降卖国的一面;又注意到其悲剧人生的根源在于阶级局限性及其民族悲观心理与时代潮流的严重背离。
【关键词】华北危局 黄郛 塘沽协定 大连—北平善后会谈 关内外通车通邮谈判
一 风雨飘摇的华北危局
日本侵略者早在明治中期,就形成了以中国为主要扩张目标的大陆政策。1927年的东方会议和《田中奏折》,将大陆政策推向一个新的阶段。“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是亦我日本帝国之存在上必要之事也。”[1]1931年,日军制造九一八事变,很快就占领了我国东北全境(图一)。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勃然兴起(图二、三)。翌年,日本侵略者一方面积极炮制成立伪满洲国;另一方面又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强迫中国签订《中日上海停战及日方撤军协定》。
1932年下半年以后,日本国内军部法西斯体制逐渐形成,更加助长了日军扩大侵略中国的嚣张气焰。1933年元旦,日军驻山海关(也称榆关)守备部队制造手榴弹爆炸事件,挑起入侵长城、察哈尔的序幕。3日,素有“天下第一关”之称的山海关被日军占领。10日,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名发表宣言,提出中国工农红军准备在“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等三个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队伍订立共同对日作战的协定,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图四)。2月23日,日伪军数万人在飞机、坦克支援下向热河发动进攻。3月4日,轻而易举地侵占了热河省会承德。蒋介石对日军进攻热河,并没有采取有力措施,所作过的一些抵抗表示,也只不过是为应付舆情而已。此时,蒋介石正在江西南昌指挥国民党军队对中国工农红军进行第四次“围剿”,正如宋庆龄所指出的,“这个政府用它的主要军队打中国的人民,任用背叛的将领还坚持不肯更动,阻止人民武装与组织义勇军来参加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图五)[2]。热河失陷后,为平息众怒,蒋介石把失地的责任完全推给张学良,劝其引咎辞职。12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准予张学良辞职及派何应钦、黄绍竑掌管华北军事指挥大权的命令。
日军在山海关、热河轻松得胜后,继续向长城各关口推进。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早在下达进攻热河的命令时,就要求不失时机地占领长城沿线的界岭口、冷口、喜峰口、古北口、罗文峪等主要隘口。3月初,日军在伪满军的配合下,分兵向长城东段各口及其附近的滦东和冀东地区前进。对此,中国守军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抵抗,尤其是喜峰口、罗文峪战斗,在当时得到各阶层人士的颂扬(图六)。《益世报》发表评论:“在此以前,许多领袖们,文的领袖们,武的领袖们,都要我们相信,中国目前要想反攻日本,恢复失地,是件绝对不可能的事。喜峰口一般英雄,又证明这个不可能实为可能……喜峰口几次胜仗,又证明收复失地,不是能不能做的问题,是肯不肯做的问题;不是有没有科学器械的问题,是有没有忠勇的问题。”[3]但是,全国军民的抗日救亡热情并没有促使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方针。3月23日,蒋介石在北平对华北高级将领说:“要以现有兵力竭力抵抗,不能希望再增加援军。”[4]4月6日,蒋介石电告诸将领:“外寇不足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如不先清内匪,则决无以御外侮”,“本总司令来赣督剿,实示有我无匪之决心,如我剿匪各将领,若复以北上抗日请命,而无意剿匪者,当以偷生怕死者视之”,“如再有偷生怕死、侈言抗日、不知廉耻者,立斩无赦”。[5]
为了配合军事进攻,日本关东军驻天津的特务机关也在华北展开了大量的“策反”活动。自民国初年以来,华北地区就是中国的多事之地,而尤其以北平和天津最为突出。这里既有北洋军阀的余孽,又有新军阀之雄辈,各派政治势力猬集,甚至还与日本侵略者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早在1933年2月23日就奉参谋本部密令潜入天津,设立特务机关,谋划华北地区的“策反”工作。他首先将华北军阀残余人物区分为蒋派、反蒋派、现状维持派和首鼠两端派四类,企图收买段祺瑞、吴佩孚、孙传芳、张敬尧、郝鹏举、石友三等失意官僚军阀等。在遭到段、吴、孙的婉言谢绝后,选得张、郝、石等,尤其以张为希望。根据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调查,板垣在短短三个月用于收买汉奸的费用就达300万日元[6]。
日本侵略者的疯狂进攻和“策反”谋略已造成华北形势危如累卵,甚至威胁到国民党在全国的统治。南京国民政府国防会议认为:“平津若失,则海关收入骤形短缩,其他一切筹款方法,亦惟有更形拮据。”[7]徐永昌也认为:“我大军若退过平津之线,即等于华北整个沦亡,人心失所依据,其促成第二满洲国亦意中事,所以决不放弃平津者此也。或谓日人得平津无办法,不知我失平津更无办法;盖仅就收入一项言之,已足制我死命,正如杀人者固不得了,而被杀者先不得了也。总之,平津失则华北亡;或谓平津纵失,亦不过一时,然数十万败兵一旦退下,人心何以维持?财政何以敷衍?”[8]因此,保全平津,必然是南京国民政府的当务之急。“华北非东北可比,立刻要影响到全国。而华北的得失,系于平津之守不守。斯时的平津,已不是军事上能守不能守问题,而是政治上欲保不欲保问题。”[9]
二 在上海的秘密接触
面对华北危局,蒋介石逐渐抛弃了“不与日本直接交涉”的誓言。九一八事变以来,由于与日本侵略者直接交涉一直为舆论所深恶痛绝,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更多地把中日矛盾的解决寄希望于国际联盟(国联)。在日军进攻长城东段各口时,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曾吁请英、美立即以最有效之方法制止日军之蛮横与暴行,但其结果令蒋介石只能无可奈何地感叹:“列强所谓助我者,仅予日本以一骂,而日本必即还我以一刀。”[10] 1933年3月27日,日本索性退出国联,可以说中国希望国联制裁日本侵略的策略已至穷途末路。28日,蒋介石与刚回国的汪精卫达成“剿共重于抗战”,汪任行政院长推行同日本直接交涉解决华北危局的协议。4月9日、11日,蒋介石连续致电邀约结拜兄弟,堪称“王者师”的黄郛到南昌晤谈,“时局艰危至此,兄等有何卓见?”“深盼兄即日命驾来南昌,群商一切。”[11]
黄郛,字膺白,是蒋介石的浙江同乡,清末时曾留学日本学习军事,在辛亥年间与蒋介石、陈其美互换兰谱结拜为兄弟。1920年起进入北洋政界,当过外交总长。1926年南下进入蒋介石麾下,1928年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因“济南惨案”善后交涉失败,退居浙江莫干山过着山居生活,研究“广义的国防中心建设计划”。1933年4月14日,蒋介石又致电黄郛,恳请其出山主持对日交涉,“兄如不愿任北事,能否以私人名义赴北方襄助?”[12]黄郛被蒋介石的诚意所感动,毅然出山,领衔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下简称“政整会”)委员长一职。“勿以为我们长可在山中做‘事外遗民’,国家垮下来将无山可入,不经努力,他日必悔,尽最后之力,则心安无怨。”[13]
黄郛受命后,先至上海秘密展开活动,一面物色人才,一面向日本驻华使馆武官辅助官根本博探询日军意图,打探日本关东军的态度。黄郛先后物色了两批人先行北上。第一批是网罗办过对日交涉的人刺探敌情,第二批是吸纳与旧军阀政客有过交谊的人实施对内怀柔敷衍。4月19日,在英国外交官的斡旋下,黄郛和张群、陈仪秉承蒋介石和汪精卫的旨意在上海与根本博秘密会谈。根本博提出,中方如果想停战,必须解除对兴隆日军的包围,从南天门撤至开平、玉田、顺义一线。何应钦得知后立即下令撤退。但关东军却电告根本博,说南天门是日军攻占的,不能作为谈判的条件,并提出中国军队撤到密云、平谷、玉田、滦河右岸,日军可以缓和攻势。正当黄郛等人与根本博商谈停战条件的时候,驻北平的日本武官永津佐比重出来插手干涉,使中日之间的停战交涉不得不转移到北平。5月12日,在汪精卫的要求下,黄郛再次与根本博会谈。根本博又无理指责中国军队攻击日军。这次由于黄郛求和心切,主动提出中国军队从新开岭撤至密云、玉田、滦州、滦河一线,并致电张群、何应钦、黄绍竑:“若节节战退,势必波及北平近郊,若大胆下一决心,用极速度撤至后方密云约二十里炮程不及之地,如牛栏山一带从事整理,则无益之牺牲,可以减少,对外之运用,较为便利。”[14] 13日,何应钦下令南天门附近阵地之中央军撤退到牛栏山一带,同时令冀东一带的何柱国、王以哲等部自唐山、丰润一线以西地区撤退。14日,黄郛第三次面见根本博,告知何应钦已同意其要求,并要求根本博向东京和关东军方面斡旋,迅速实现停战。
黄郛出山与日交涉的开始,标志蒋介石、汪精卫对日和缓路线的正式形成。正如日本侵略者判断的那样,“惟以关东军之急速追击,而造成之内外情势之恶化,已至无法再事拖延之地步,于是授权素有亲日家之称又非国民党党员之黄郛,北上全权处理华北问题。黄郛之出马,确为中方让步之第一阶段,黄郛与我武官之间之交涉,纵无具体的进展,但彼我在精神方面,已有和蔼之接触,则属事实。”[15]
三 《塘沽协定》的最后签订
1933年5月17日,黄郛抵达北平。21日,日军攻下香河,前锋已到离北平东面通县只有七公里的地方。何应钦打算放弃北平,将军政机关迁到长辛店。黄郛对停战也有些绝望,在22日的电文中说:“日方态度骤变,既往工作尽付流水……,北平既入战区范围,政整会自无工作余地,现虽尚未成立,拟至必要时即随军事机关转进,或即南旋面陈经过。”[16]晚10时,汪精卫回电黄郛:“欲谋停战,须向对方问明条件,由负责长官决定其可答应与否。弟以为除签字于承认伪国,割让四省之条约外,其他条件,皆可答应。且弟决不听兄独任其难,弟必挺身负责。乞速与敬之、季宽、岳军(引者加:何应钦、黄绍竑、张群)诸兄切实进行为盼。”[17]黄郛便以这封电文为尚方宝剑,决定留下等待绝处逢生的时机。其实,日本侵略者也看到自己的战斗力殆已用尽。东京参谋本部在22日也致电关东军,促其进行停战谈判。晚11时,永津佐比重受武藤信义之命,急忙准备停战交涉,让海军武官藤原喜代间居中安排,约请黄郛谈判。经过彻夜讨论,在23日凌晨4点半,商得停战之谅解。其经过,藤原喜代间有如下记载:“廿一日何应钦氏已作出退出北平之准备,黄郛茫然无策,关东军恐失去有利机会。余依陆军意愿,于廿二夜托李择一,介请黄郛在海军武官宿舍会晤,中山(详一)代办在座。我等要中国速断,谈话两三小时后,黄氏申请停战之希望既明,乃招永津武官出谈,至廿三早四时半,始制定停战条件。”[18]
25日,按照日方提出的三步屈辱停战办法,黄郛、何应钦责令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高级参谋徐祖贻前往密云请求停战,与日方签订了内容包含“日本军为认识诚意,第一步随时以飞行机侦察及其他方法视察中国军之撤退状况,但中国方面对此予以保护及一切之便宜”等的停战《觉书》[19]。对此等带有战胜者对失败者口气、带有极大侮辱色彩的《觉书》,黄郛、何应钦没有表示更多的惊讶,并于26日下午快速决定派参谋本部厅长熊斌临时以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总参议衔为正式谈判代表。30日,中、日双方代表在塘沽正式举行谈判(图七)。关东军派副参谋长冈村宁次为首席代表。在会上,冈村宁次首先提出事先准备好的协定草案,并声称此乃关东军的最后方案,不容只字更改,要求中国代表必须在一个半小时内作出答复。主要内容共四项:“ 一、中国军即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镇、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之地区,不再前进;又不行一切挑战扰乱之举动。二、日本军为确悉第一项实行之情形,可用飞机或其他方法施行视察,中国方面应行保护并予以便利。三、日本军确认中国军已撤至第一项协定之线时,即不再越该线续行追击,且自动撤归还至长城之线。四、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域内之治安维持,以中国警察机关任之。”[20]同时,方案也要求设立的警察机关,不能用刺激日本侵略者感情的武力团体。熊斌等面对冈村宁次盛气凌人的姿态,相持到10点50分,最后一字不改地在日方提出的协定草案上签了字,史称《塘沽协定》。在下午14点时,中、日双方代表继续开会,针对中方在上午所提意见书,双方另作一个备忘录,内容是:“万一撤兵地域有妨碍治安之武力团体发生,而以警察力不能镇压之时,双方协议之后,再行处置。”[21]此外,双方还达成了四项口头密约:丰宁西南面之骑兵第2师,望即撤去;平、津附近之40个师,望即调往南方;白河附近堑壕及其他军事设备,望即撤去;彻底取缔排日。[22]
《塘沽协定》作为一个停战协定,虽然促成了华北地区的短暂休战,但是无论是其产生过程,还是文字内涵,都使中国遭受了极大的耻辱,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尊严、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备忘录和口头密约的规定,实际上等于撤走中国在华北地区的防务。显然,“赢得休战不是赢得和平”[23] ,关东军转而握有华北安危的锁钥。
四 大连—北平的善后会谈
《塘沽协定》签订后, 政整会于1933年6月17日在北平正式成立。黄郛主持典礼大会并讲话,称:“郛以菲材,负兹艰巨,困心衡虑,昕夕筹维,以为目前切要之图,首在安定人心,保全疆土。其次则使战区恢复常情。”[24]而日本却继续以武力为后盾,借商谈停战善后事宜之便,从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不断向华北渗透。
按照《塘沽协定》,在停战后日军应“自动概归还于长城之线”,中国军队则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镇、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两线之间的中间地带作为非武装区,也通称战区,包括临榆、抚宁、昌黎、遵化、迁安、蓟县、怀柔、密云、顺义、卢龙、滦县、丰润、玉田、乐亭、宁河、兴隆、平谷、通县、香河、宝坻、三河、昌平等22县及都山设治局,由中国警察机关负责维持治安。虽然日军已在6月5日开始向关外移动,却故意寻找借口一再拖延。更有甚者,日军把撤出地区交由伪军李际春部接防,并扶持伪军石友三、郝鹏举等部在冀东进行骚扰。在战区内,日伪军横行,土匪蜂起,百姓流离失所,使战区接收工作难以进行。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致电黄郛、何应钦,陈述接收战区困难时称,“即令收回各县,仍然不能行使职权”,要求“暂缓接收,以免徒生枝节”[25]。
22日,黄郛指派殷同、雷寿荣去长春与日本代表小矶国昭、冈村宁次接触商量《塘沽协定》的履行问题,口授会商要点如下:“(1)停止平津上空之飞机成队飞行,以安人心。(2)主张从速接收战区各县政,以便遣送难民回籍。(3)关于撤兵区域内李际春非法等部队之处理。(4)北宁铁路之从速接收。(5)关于察哈尔方面各问题。”[26]双方在会谈中没有发生大的争论,并商得如下主要结论:日本方面禁止无意义之飞行;中国军队不进入地域难民之遣归,日本方面以好意听中国方面自由处理;从伪军李际春部中选择3000到4000人改编为中国警察队,配置于中国军队不进入地区内,以李际春为保安司令,其余作为暂编旅移驻他处;北宁路的接收由中国北宁路局与伪满奉山路局交涉。也就是说,只要日军认为有意义,仍然可以自由飞行;伪军李际春部仍然得以保存等。29日,永津佐比重从长春返回北平,与黄郛、何应钦商定双方派员赴大连为具体之商议。
6月30日,黄郛、何应钦派殷同、雷寿荣及与李际春有私谊的薛之珩赴大连与日方代表冈村宁次、喜多诚一开始具体商谈。7月2日,“大连会谈”开始。6日,会议结束,并无正式文件发表,大致达成妥协:一,所有战区以内之伪军,三分之二遣散,三分之一收编,为河北省保安队,仍驻滦东;二,在日军逐渐撤退后,北宁路的芦台至山海关段仍由中国方面管理;三,自10日起,中方依次接收滦东、平北地区[27]。7月19日,黄郛为了求得同日本侵略者的妥协和苟安,答应支付编遣善后款48.4万元,并委任李际春为战区军事编练委员长。各县接收自7月中旬开始,但因部分县内日军未撤走、伪军盘踞和县境跨越长城线等原因,日军刁难蛮横,有的进展缓慢,有的根本就没有收回。都山设治局,由于在长城线外,日方以长城为伪满洲国的国境,不承认其为战区,强行将其划入热河省,改名青龙县,拒绝中方接收。即使在名义上收回了的地域,黄郛也必须精心挑选与日本关系亲近的殷汝耕、陶尚铭分别任蓟密区、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
日本侵略者欲壑难填,并不满足已获得的侵略权益,继续谋求加强对华北的影响力和支配力。11月6日,冈村宁次和喜多诚一等抵达北平,先后拜会黄郛、何应钦。当日晚上,黄郛在北平外交大楼设宴招待冈村宁次一行,并请何应钦、殷同、殷汝耕、陶尚铭等作陪。宴会后,根本博向黄郛出示《关于北支善后交涉商定案》草案一份,并声言本案为关东军再三审议决定者,中方只可以为文字之修正。主要内容四项:一,在长城各隘口警备权属于日、伪满洲国,凡有日军驻屯之住民地不配置武装团体的谅解下,中国可以从速接收不含长城线之长城以南以西之区域;二,在接收区域内,中国允许伪满洲国在山海关、古北口、喜峰口、潘家口、冷口、界岭口设置必要的各种机关,并给以最善意的援助; 三,中国在山海关、石门砦、建昌营、抬头营、冷口、喜峰口、马兰峪、古北口向日军提供必要的土地房屋,以备日军暂时驻屯;四,中国迅速委派代表与伪满洲国交涉通商贸易、交通通讯、航空联络等问题[28]。7日上午,中方代表黄郛、何应钦、殷同、殷汝耕、陶尚铭与日方代表冈村宁次、喜多诚一、菊池、根本博、柴山兼四郎、中山详一、花轮义敬开启“北平会谈”。由于日方在谈判中始终采取外交高压政策,动辄以破裂相要挟,双方代表在前后合计七轮会谈之后形成了《关于停战协定善后处理之会谈事项》及《关于本会谈之谅解事项》两份非正式文件。与日本最初的提案比较,实质内容完全一样。
善后会谈名为解决《塘沽协定》的善后事宜,实则日本进一步威逼南京国民政府和华北当局承认其侵略事实,如承认长城为伪满洲国的边界,允许伪满洲国在长城各口设置机关,要求中方与伪满洲国交涉等。事后,黄郛既痛苦,又担心,致电蒋介石,“郛等殚精竭虑,仅乃获此,欲为国家多争尺寸之失地而未能,彷徨午夜,相对凄其”[29]。
五 关内外通车通邮的艰难交涉
关内外通车通邮问题对南京国民政府和华北当局来说,更是一剂难服的苦药,他们都担心给人以承认伪满洲国的印象,引起国内舆论的反对和在国际上造成不良后果,而有意拖延回避。“北平会谈”后,日本侵略者更是加紧催促实行关内外通车、通邮和在长城各口设立税卡,以造成对于伪满洲国事实上的承认,并以此向华北地区加紧渗透和扩张。
1934年4月9日,日本武官柴山兼四郎发表谈话:“然中国方面曾于过去十个月间凡属根据协定之各种问题,从未进展。如通车通邮等问题,倘经解决,则享受利益者当为中国本身,至为明显。究竟是否中国对于上述情形认识不足,或系故意延不履行,此吾人认为遗憾。然为暂时计,或局部计,亦当有任何处理之法,中国当局岂无办理可言,殊难置信。”[30]根据“大连会谈”约定,中国收回关内失陷路段,北平至山海关段已在1933年8月15日恢复全线通车,来往于关内外的车辆仅需在山海关车站换车而已。可是,日本侵略者仍不满足,要求关内外实现直通车。蒋介石、汪精卫担心如果再拖延,势必会予日本以借口,决定将此事交由黄郛具体处理。5月12日,黄郛电令殷同先与日方作私人会晤,交换意见。14和15日两天,中、日双方代表在山海关进行了正式会谈,并商定了通车具体方案,即:中日双方共同投资组织东亚通运公司,资金各半,总经理、副经理交替选派,利润及损失亦由双方分担,列车乘员在山海关相互交换,每日由北平、奉天对开一列车[31]。7月1日,关内外正式通车。
通邮问题紧接着也被提上议事日程。1934年8月12日,黄郛在牯岭与蒋介石拟定了“通邮会商步骤”。9月29日,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特派高宗武、余翔麟、殷同、李择一与日方代表藤原保明、仪我诚也、柴山兼四郎在北平开始正式会谈,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并几度陷入僵局:一,邮票问题。中方不承认伪满发行的邮票,即使表示“邮资已付”的印花,也应避免有“满洲”字样或不适当的花纹。日方开始要求使用伪满邮票,后来提出票面只用“邮政厅”但仍印“满洲邮政”水印。二,交换邮件及日戳问题。中方坚持不与伪满直接交换邮件,日戳上不用“新京”而用“长春”并盖公历。对此,日方坚决拒绝。三,邮件种类问题。中方主张只允许普通邮件,而日方提出应包括快信、挂号、汇兑在内。11月21日,外交部次长唐有壬奉命到达北平,与黄郛等讨论会商与日交涉问题。23日夜,日方提出通邮七条大纲,要求中方立即给予“同意”或“不同意”的答复,否则就宣告谈判破裂。在日方压力下,中方代表在24日凌晨完全接受了日方提议。12月14日,中日双方终于在所谓“不为成文规定”的原则下达成通邮办法和谅解事项:一,通邮由双方邮政机关进行,在山海关、古北口设立转递机关;二,不使用伪满邮票,而另用特种邮票,上面须无“满洲国”或“满洲”字样;三,邮戳用欧文;四,邮资由双方自定;五,通邮事务之文书尽量标用公历,不表示“满洲国”或“满洲”字样;六,通邮实施期为1935年1月7日,包裹、汇兑自2月1日实施;七,通过西伯利亚之邮件照旧办理[32] 。1935年1月10日,关内外实行通邮。2月5日,关内外的电信联系恢复,6月1日又恢复了电话联系。
关内外通车通邮谈判,蒋介石、汪精卫和黄郛虽一再强调以不承认伪满洲国为原则,在协定中也尽量排除伪满洲国字样,但在事实上已是对伪满洲国的默认。
六 结 论
随着华北危局的逐步发展,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呼声越来越高(图八、九、一○)。蒋介石、汪精卫和黄郛却一直坚持委曲求全的精神,企图通过谈判、磋磨,甚至乞求等方式,谋得妥协苟安,结果导致日本侵略者得寸进尺,嚣张气焰愈盛。1935年,日本侵略者在华北制造河北、张北等恶性事件,后来终于有了殷汝耕的汉奸政权,华北局势更加危急。2月,黄郛托病黯然重返莫干山,于1936年12月6日上午9时20分辞世而去。蒋介石在1945年12月5日为追念黄郛特予褒奖令:“故国民政府委员黄郛,志虑忠诚,识量宏远,尽瘁革命,始终弗渝。……迨敌人据我辽沈,胁我平津,寇患日深,群情惶惑,不避险阻,力任艰难,隐忍求全,用纾祸变,心孤事苦,尤人所难。值此抗战胜利之秋,缅维当年艰屯之会,公忠谋国,端赖老成,樽俎折冲,功同疆场。”[33]
从客观历史条件来讲,在敌军重兵压境之时,黄郛仅凭口舌为弭兵之计,其间遭遇的艰难困苦,迂回曲折,可想而知,难怪自叹“力薄难回劫后灾,莫干小住赋归来,檐头春雨连宵滴,塞外迷云那日开”[34]。但是,就对日交涉的结果来看,站在民族大义、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讲,无疑是失败的。导致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黄郛长期沉湎于民族悲观主义之中,对军国主义统治下的日本既钦佩又羡慕,过犹不及,把日本看得过于强大,在与日方代表交涉时,几乎丧失了敢于战斗的勇气。1933年10月,日本满铁代表山井格太郎询及黄郛的“日本人观”。黄郛回答:“贵国民众的心灵深处潜在的民族思想”,“人们对皇室抱有崇高的信仰,这在他国人看来是无法想象的”,“贵国人有一种打开难关、臣服强敌的气概”[35]。对于来自日本侵略者的侵扰,他主张尽早谋求与日本侵略者妥协谋和,曾说:“对日本人,只宜用柔术,不宜施硬拳,所谓柔能胜刚;不可呈一时的意气,以闯出无穷的大祸,无可挽救”[36]。可是,黄郛主张以柔胜刚的妥协不仅丝毫没有阻止和延缓日本侵略者的疯狂侵略,反而刺激了他们更加贪婪的本性。与黄郛打交道的日本外交官得出的结论是:“华北官方对我之态度,无论军政当局,均以不惹是生非勉维现状为主旨,凡百我不苛求,一切均可迎刃而解,可谓之对我系妥协态度”,“以后对华任何交涉,无论巨细,与向地方或中共中央交涉,应贯彻一贯的强硬主张,决不可犹豫,虽迁延时日,亦必能获得最后胜利也。”[37]我国爱国民主先驱章乃器曾发表时事评论:“过去外交上的妥洽路线,是便于敌人完成‘以华灭华’的策略,是便于他们自己做敌人的刽子手,已经在事实上得着证明了。”[38]
第二,黄郛坚持反苏反共,无视将社会主义苏联作为抗击日本侵略者盟友的可能,和蒋介石、汪精卫等一开始就主张对日妥协求和态度,支持蒋介石的“安内”计划,也注定了其对日交涉的最终失败结局。在黄郛看来,“苏联顾问太专制了,共产党太可怕了。”[39] 1934年5月9日,黄郛在致汤尔和的电文中说:“夫中国如欲联俄倒日,不啻助日。盖外则世界各国鉴于东亚大陆将全部赤化,必一致助日,以遏此不可收拾之局。”[40]黄郛北上解决华北危局,蒋介石、汪精卫交待的底线就是保住平津,阻止中日之间的事态扩大,稳定华北局势,以便集中力量“安内”。历史事实已经证明,由于“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的长期推行,严重伤耗了中华民族的元气。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黄郛毅然出山北上,主持对日交涉,助长了蒋介石贯彻执行此方针的决心和信心,方便蒋介石更加专注于“剿共”计划,摧残民众组织,压迫抗敌言论。
注释:
[1] 章伯锋、庄建平:《抗日战争》第1卷(从九一八到七七),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3、24页。
[2] 宋庆龄基金会:《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00页。
[3] 《喜峰口的英雄》,《国闻周报》第10卷第12期,1933年3月27日。
[4] 李勇、张仲田:《蒋介石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第211页。
[5]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第35、36页。
[6] 梁敬錞:《日本侵略华北史述》,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1页。
[7]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第646页。
[8] 沈亦云:《亦云回忆》下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472页。
[9] 同[8],第467页。
[10] 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中日关系八十年之证言》第9册,台北“中央日报社”,1978年,第107页。
[11] 同[8],第450页。
[12] 同[8],第451页。
[13] 同[8],第452页。
[14] 沈云龙:《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下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第548页。
[15] 同[1],第502页。
[16] 同[8],第479、480页。
[17] 同[14],第559页。
[18] 同[6],第21页。
[19] 同[14],第563页。
[20] 同[14],第569页。
[21] 同[8],第468页。
[22]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卷,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第276页。
[23] 马季廉:《停战与华北前途》,《国闻周报》第10卷第22期,1933年6月5日。
[24] 同[14],第577页。
[25] 张篷舟:《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第一卷(1932-1934年),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79页。
[26] 同[14],第581页。
[27] 同[14],第590、591页。
[28] 同[14],第638、639页。
[29] 同[14],第659页。
[30] 同[14],第722页。
[31] 吴东之:《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1911-1949年)》,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11页。
[32] 同[14],第814、815页。
[33] 同[14],第1035页。
[34] 同[14],第731页。
[35] 钟山:《1933年黄郛与山井格太郎谈话录》,《档案与史学》1996年第1期,第34页。
[36] 曾扩情:《何梅协定前复兴社在华北的活动》,《文史资料选辑》第14期,中华书局,1961年,第138页。
[37] 杜春和、耿来金:《1935年日本驻华总领事会议记录》,《近代史资料》第86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131-158页。
[38] 章力凡编《章乃器文集》下卷,华夏出版社,1997年,第172页。
[39] 同[8],第354页。
[40] 同[14],第733页。
(责任编辑 朱亚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