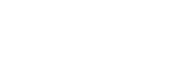盂鼎是铸造于西周早期的青铜重器,作器者盂,为周康王时期战功显赫的重臣。盂鼎器形厚重雄伟,铭文篇长且学术价值重大,因此自晚清出土以来,即备受关注,名满天下,其流传经历也充满了传奇色彩。
盂鼎的出土年代,一般认为是在清代道光年间,一说是嘉庆道光之际。出土地点,则有岐山礼村和眉县礼村两种说法,“礼村”多认为是现在岐山县的礼村,也有人认为是今眉县“李村”的误写。盂鼎出土后,即为岐山县乡绅所得,得主一说为宋氏,一说为郭氏。岐山县令周赓盛(任职于1838—1842年)得到消息后,“遽豪夺去”。周在岐山做官时名声很臭,以致“人心讟怨,道路以目”(清《岐山县志》),看来此类强取豪夺行为是他的家常便饭。周赓盛得到盂鼎后,秘不示人,但有时会应别人之求为其打制拓片。后来,周赓盛调任三原县令,盂鼎可能又随其迁移,以后就失去消息了。1873年,盂鼎再次“现世”,被陕甘总督左宗棠的幕僚袁保恒(字筱坞)以600余金(一说700金)购得。盂鼎如何复出,有两说:一是周赓盛死后,盂鼎从他家流出;一是盂鼎自周手中流出后又到了岐山宋氏手中,再被宋氏卖出。实情目前已无法求证。袁保恒是清末重臣、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的堂叔,平时也搞些收藏,到陕西做官后与当地一些文物贩子有来往,盂鼎可能就是通过他们买到的。但袁此次购鼎,并不是为了个人收藏,而是秉承上司左宗棠之意而为。左宗棠购买盂鼎的初步想法不甚明了,但买入后却有意将它赠送给好友潘祖荫(字伯寅)。左如此慷慨是有原因的。原来,潘祖荫是左宗棠的恩人。1859年,时任湖南巡抚幕僚的左宗棠被人上告多行不轨,以致龙颜大怒,几乎掉了脑袋;当时在朝为官的潘祖荫等人上疏保左,使左不仅未受处分,还因祸得福,走上飞黄腾达之路。左宗棠自然对潘祖荫心怀感激,他知道潘嗜爱金石、“有三代文字之好”,因此有意把盂鼎送给他。不料一番好意刚开始就碰了钉子,潘祖荫在看过左宗棠寄来的盂鼎拓片后,竟怀疑是赝品。左很无奈,但认为“殊器不可令其勿传”,于是考虑把盂鼎送入关中书院收藏。不久后,潘祖荫通过与知情友人的通信,最终确认盂鼎为真。一旦确认,则热情似火,立刻写信催促左早日送鼎入京。左于是又托袁保恒办理这件事,打算用小车运送。但这一过程却出奇的长,半年过去了还没有消息,潘祖荫十分焦急,一度怀疑自己是否能够如愿得到盂鼎。其实,在此期间左宗棠和袁保恒因公事意见不合发生了很大的冲突,送鼎之事一拖再拖很可能与此有关。1875年1月初,在潘祖荫的翘首以盼下,盂鼎终于被送到了京城潘家,成就了潘、左友谊的一段佳话。潘祖荫得到盂鼎后,托人精刻了“南公鼎斋”和“伯寅宝藏第一”两方印,足见其重视程度。此后,盂鼎一直藏于潘家,时常有人前去瞻仰。1890年,潘祖荫病死,几年后,他的夫人也去世了。潘祖荫一生无子女,因此其家产由小他40岁的弟弟潘祖年继承。潘祖年雇船将包括盂鼎在内的潘氏藏品通过水路运回老家苏州。失去官位庇护的潘家为了保护盂鼎和大克鼎(潘祖荫晚年获得的另一重器),立下了“谨守护持,绝不示人”的家规。清代末年,酷好古物的端方任两江总督,企图夺取二鼎,终未得逞。潘祖年也没有子嗣,于是过继了一个孙子,并为其娶媳潘达于(原姓丁)。不久孙、祖二人先后去世,潘达于成为一家之主。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护宝,潘家将盂鼎和大克鼎埋入地下,然后全家到上海避难。日寇攻占苏州后,专门到潘家劫掠文物,但没有找到两鼎。1951年,潘达于将千辛万苦保护下来的盂鼎和大克鼎无偿捐献给了新中国,两鼎随后入藏上海博物馆。1959年国庆十周年之际,盂鼎调拨中国历史博物馆。潘家护鼎和献鼎的感人事迹,多年来一直为人称颂。2004年,上海博物馆隆重地为潘达于庆寿,举办了“百岁寿星潘达于捐赠大盂鼎、大克鼎回顾特展”,作为国家博物馆藏品的盂鼎南下上海,与大克鼎团圆,与潘达于团聚,一时传为美谈。
盂鼎又叫“大盂鼎”,很多人可能不理解,需要做一下解释。原来,与盂鼎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铜鼎,作器者也是盂,铭文字数比盂鼎多(大约400字),但字体较小。这件鼎很快就失传了,只留下一个不清晰但却很重要的铭文拓片(顺便说一句,我们之所以能将盂鼎确定在康王时,正是根据这个铭文的提供的信息)。最初,两件鼎同被称为“盂鼎”,后来为了区分,就将字大的鼎叫做“大盂鼎”,字小的鼎叫做“小盂鼎”。因此,盂鼎是因为字体(而不是形体)较大才被称为大盂鼎。有趣的是,根据清代人的记述,小盂鼎在形体上反而要大于盂鼎,因此当时的著名学者陈介祺在提到二鼎时,就以“大盂鼎”之名来称呼小盂鼎。严格来说,将盂鼎叫做“大盂鼎”并不完全合适,只是相沿成习,就一直叫了下来。
盂鼎在清代又被称为“南公鼎”,这是因为从其铭文中可知作器者盂的祖先是南公。南公是个什么人物?据西周晚期的南宫乎钟铭文可知道,他是西周南宫氏的始祖,应该就是周文王时候的重臣南宫括(或写作南宫适),熟悉《封神演义》的朋友对他应该不陌生。据《尚书》,周成王去世、康王即位时的顾命大臣中,有一个南宫毛,很可能是盂的父辈。盂显赫的地位与其辉煌的出身很有关系。
盂鼎的长篇铭文,自晚清以来广为传颂。有学者认为,盂鼎291字的铭文甚至要比毛公鼎铭文将近500字的铭文还要重要,这主要是因为盂鼎的时代较早,反映的内容因此也更有价值。我们知道,周人有所谓“天命观”,即认为周灭商出于“天命”,也就是说,是上天的旨意;这种观念在古书中多次提到过,但盂鼎铭文中的相关内容却是目前所见的最早反映这种观念的实物资料。商人之所以灭亡,据古书中周人的说法,是纵酒无度,我们都很熟悉的商纣王就有“以酒为池”的恶迹;盂鼎铭文关于商人纵酒亡国的内容,不但可印证古说,也是目前发现的唯一的实物证据,直观的再现了周人的原始话语。此外,周王嘉奖盂,赏赐他土地奴仆的记载,也是很重要的史料。总之,盂鼎对研究西周早期的社会极具价值,而其时代距离传统文人(包括孔子)所向往的周初盛世又很近,难怪陈介祺在给潘祖荫的信中激动地说:“盂鼎……真三千年来之至宝,成康以后之人,恐即不得见,况秦汉乎,况宋以后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