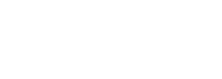

为给中国共产党一百周年华诞献上一份深情礼赞,中国国家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将共同促成大盂鼎、大克鼎联袂特展在上博与国博先后举办,同时在学术研讨会、宣传教育和文创开发等领域开展深入合作。
青铜大鼎历来为国之重器,社稷象征;有铭文者,更用以称扬先祖之美,明示后世之用。大盂鼎是周康王时器,大克鼎是周孝王时器。二者铭文均是研究西周社会政治、经济的重要资料。1951年,大盂鼎、大克鼎由潘达于先生无偿捐献国家。1959年,大盂鼎应征北上,入藏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无论是在当时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中国通史陈列”,还是如今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古代中国”基本陈列和“中国古代青铜艺术”展,大盂鼎始终在重要展线上“公诸人民”。这既是以实际行动履行国家大馆的职责使命,也是达成潘先生在把大鼎捐献国家时所表达的“俾全国性之文物得于全国重要区域内,供广大观众之观瞻及研究”之心愿。
国博上博还将联合推出一系列宣传推广活动,包括深度报道、展览直播、文物讲解短视频等,并合作研发相关文创产品,从多角度阐释中国古代艺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

盂鼎立耳,折沿,垂腹,三蹄足。口沿下饰6组饕餮纹,“几”形角,身、爪与首分离,中有扉棱;蹄足上部饰卷角饕餮纹,有扉棱。高101.9、口径77.8厘米,重153.5千克。铭文铸于器内壁,共十九行291字(含合文5)。铜鼎一般用来煮牲肉以供祭祀和其他礼仪活动。盂鼎这类大型铜鼎所煮应为大型牲体。
盂鼎因作器者为盂而得名。盂是周王朝重臣,出身南宫氏,为开国元勋南公(南宫适[括])之孙。盂鼎是盂为南公所作器,因此曾被称作“南公鼎”。盂鼎又称大盂鼎,是为了与另一件盂所作鼎(“小盂鼎”)做区分。这件鼎与盂鼎同出,后归另一位岐山知县李文翰(安徽宣城人),经太平天国运动,已失传,只留下一个不清晰但却十分重要的拓本;其铭文字数(近400字)多于盂鼎,但字体较小,故被称作“小盂鼎”,盂鼎相应被称作“大盂鼎”。但论体量,“小盂鼎”则未必小于盂鼎。著名金石学家陈介褀即以为 “小盂鼎”形体大于盂鼎,反而称其为“大盂鼎”。著名学者杨树达曾根据两鼎现存铭文完残情况,称盂鼎为“全盂鼎”,“小盂鼎”为“残盂鼎”。这一名称并未流行。


盂鼎的出土年代,一般认为是清道光年间(1821—1850),一说嘉庆、道光之际。已知最早的铭文拓本出现于“道光庚子辛丑间”(1840—1841),是为盂鼎出土年代的下限。盂鼎的出土地点,主要有岐山县礼村和眉县礼村两种说法。岐山县确有礼村,眉县则无礼村,所以有学者据此认为鼎出自岐山;但也有学者认为“礼村”为“李村”之误,鼎应出自眉县(1955年眉县李村曾出土盠驹尊、盠方彝[大小2件]等青铜器,盠驹尊和小盠方彝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总体看,盂鼎出自岐山县的可能性更大。
盂鼎出土后为岐山县乡绅所得,得主一说为宋氏,一说为郭氏。岐山知县周赓盛(1838—1842在任)得知后强取豪夺,据为己有,虽秘不示人,却时常为人作拓,部分早期拓本即由此而来。后来,周赓盛调任三原知县,将盂鼎携至三原。1849年周赓盛被撤职查办后,盂鼎自其家流出,为岐山宋金鉴(1825—1863)所得。目前流行的说法是,盂鼎最早即为宋金鉴所有,一度被周赓盛夺去,又复归宋金鉴。但从宋的出生年看,这一说法很可疑。约1872年,盂鼎为袁保恒(1826—1878)所得。袁保恒是袁世凯的堂叔,当时在陕甘总督左宗棠(1812—1885)手下任职,他与宋金鉴为同榜进士,其能从宋家得到盂鼎应与此有关。1873年,在左宗棠居中联络后,袁保恒同意将盂鼎转售于潘祖荫(1830—1890)。潘祖荫为江苏吴县人,长期在京城为官(官至工部尚书),嗜爱金石,“有三代文字之好”;他曾对左宗棠有恩,因此后者热心促成此事。有人认为左宗棠也是盂鼎的藏家之一,是不对的。1875年1月初,盂鼎被运至京城潘宅。潘祖荫得到盂鼎后,对外采取开放态度,因此时常有人前往潘家观摩宝物。1890年,潘祖荫病逝,几年后他的夫人也去世了,因无子女,其家产由弟弟潘祖年继承。潘祖年将包括盂鼎在内的潘氏藏品运回老家苏州。潘祖年也无子嗣,于是过继了一个孙子,并为其娶妻潘达于(原姓丁)。祖孙二人去世后,潘达于成为一家之主,她在抗日战争期间为守护国宝付出了艰苦的努力。1951年,潘达于将盂鼎和大克鼎(1890年出土于陕西扶风,为潘祖荫晚年获得的另一重器)无偿捐献给国家。两鼎随后入藏上海博物馆。1959年盂鼎调拨中国历史博物馆,长期展出。2004年,上海博物馆隆重举办“百岁寿星潘达于捐赠大盂鼎大克鼎回顾特展”,作为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品的盂鼎南下上海,与潘达于和大克鼎团聚,一时传为美谈。



据器物风格,可判定盂鼎为西周早期器;据铭文,知其作于某位周王的二十三年。“小盂鼎”作于同一位周王的二十五年,铭文中出现“用牲啻周王、武王、成王”,可知这位周王为周康王。因此,盂鼎的时代为周康王二十三年(据“夏商周断代工程”公布的年表,为公元前998年)。
铭文如下:
唯九月,王在宗周,命盂。王若曰:“盂!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在武王嗣文作邦,辟厥匿,匍有四方,畯正厥民,在于御事, 酒无敢
酒无敢 ,有祡烝祀无敢扰,故天翼临子,法保先王,匍有四方。我闻殷坠命,唯殷边侯、田与殷正百辟,率肆于酒,故丧师已。汝妹辰有大服。余唯即朕小学,汝勿逸余乃辟一人,今我唯即型禀于文王正德,若文王命二三正。今余唯命汝盂召荣,敬拥德经,敏朝夕入谏,享奔走,畏天威。”王曰:“而,命汝盂型乃嗣祖南公。”王曰:“盂!乃召夹死司戎,敏誎罚讼,夙夕召我一人烝四方,雩我其遹省先王受民受疆土,锡汝鬯一卣,冂衣、巿、舄、车、马。锡乃祖南公旂,用狩。锡汝邦司四伯,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锡夷司王臣十又三伯,人鬲千又五十夫,
,有祡烝祀无敢扰,故天翼临子,法保先王,匍有四方。我闻殷坠命,唯殷边侯、田与殷正百辟,率肆于酒,故丧师已。汝妹辰有大服。余唯即朕小学,汝勿逸余乃辟一人,今我唯即型禀于文王正德,若文王命二三正。今余唯命汝盂召荣,敬拥德经,敏朝夕入谏,享奔走,畏天威。”王曰:“而,命汝盂型乃嗣祖南公。”王曰:“盂!乃召夹死司戎,敏誎罚讼,夙夕召我一人烝四方,雩我其遹省先王受民受疆土,锡汝鬯一卣,冂衣、巿、舄、车、马。锡乃祖南公旂,用狩。锡汝邦司四伯,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锡夷司王臣十又三伯,人鬲千又五十夫, 迁自厥土。”王曰:“盂!若敬乃正,勿废朕命。”盂用对王休,用作祖南公宝鼎。唯王廿又三祀。
迁自厥土。”王曰:“盂!若敬乃正,勿废朕命。”盂用对王休,用作祖南公宝鼎。唯王廿又三祀。
铭文记录了周康王在宗周对盂的一次册命,大致内容是:康王追述了文王受天命和武王建邦的历史,指出纵酒是商朝灭亡的原因;勉励盂效法其祖南公,恪尽职守,夙夜在公;赏赐盂鬯酒、舆服和南公之旂,以及奴仆1700余人;盂感念王之册命,为祭祀南公而作宝鼎。
盂鼎铭文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商代后期至西周初年的青铜器铭文布局不甚规整,字体大小不均匀,多肥笔和波磔;而以盂鼎为代表的西周早期后段铭文则布局逐渐规整化,文字排列较整齐,字体大小较均匀,只有少数字有肥笔现象。盂鼎的长篇铭文分成左右两部分,布局优美,书风瑰丽,是西周金文的杰出代表,是金文艺术的典范之作。
盂鼎是现存最大的青铜鼎之一,也是体量最大的商周青铜礼器之一。厚重雄伟,磅礴大气;纹饰虽不繁缛,但朴素典雅,别有韵味;制作精良,在铸造难度较大的大型铜器中是不多见的。
盂鼎又是罕见的长铭器,在现存青铜器中铭文字数仅次于毛公鼎(497字)、中山王 鼎(469字)、中山王
鼎(469字)、中山王 方壶(450字)、逑盘(373字)、散氏盘(350字)、四十三年逑鼎(一组,318 — 321字),多于大克鼎(290字)、多友鼎(278字)等。
方壶(450字)、逑盘(373字)、散氏盘(350字)、四十三年逑鼎(一组,318 — 321字),多于大克鼎(290字)、多友鼎(278字)等。
在上述长铭铜器中,除盂鼎之外,时代最早也是西周晚期,较盂鼎晚百余年,因此盂鼎之长铭更显珍贵。西周成康时期是公认的盛世,被称作“成康之治”,尤为儒家所推崇,盂鼎正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代表性物证,无怪乎陈介祺在给潘祖荫写信时激动难抑地说:“(盂鼎)真三千年来之至宝,成康以后之人,恐即不得见,况秦汉乎,况宋之后乎!今人何如是之幸,斯器又何为而出,殆天之为矣!”著名学者陈梦家曾高度评价盂鼎说:“所见铜器中的重器,此鼎为第一瑰宝。铭文之长虽不及毛公鼎,但内容更为重要而形制厚重雄伟。此器重量不及殷代的司母戊方鼎和大克鼎,而制作精于后者。制作、铭文和体量又都超过虢季子白盘。”有人将盂鼎与同为晚清时期发现的毛公鼎、散氏盘、虢季子白盘合称“晚清四大国宝”,可谓名副其实。
盂鼎及其铭文对西周史和青铜器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可列举如下几点。
第一,盂鼎制作于周康王二十三年,是一件典型的青铜器“标准器”,可作为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的重要参考品。
第二,铭文记录了周康王时期的一次“册命”。册命礼是维持周代“封建”等级制度的重要手段,是当时最主要的礼仪之一,多见于西周金文。盂鼎铭文是目前已知记载册命礼最早的文献,是研究周代礼制的重要资料。
第三,铭文关于商人纵酒亡国的内容,印证了《尚书·酒诰》等文献的相关记载,并直观再现了西周早期周人的原始话语。
第四,铭文记载周王赏赐盂大量臣仆(“邦司四伯,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夷司王臣十又三伯,人鬲千又五十夫”),其中“人鬲”(多被认为是奴隶)合计多达1709人,为此类赏赐已知数量最大者。这一记载无疑是研究周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的重要史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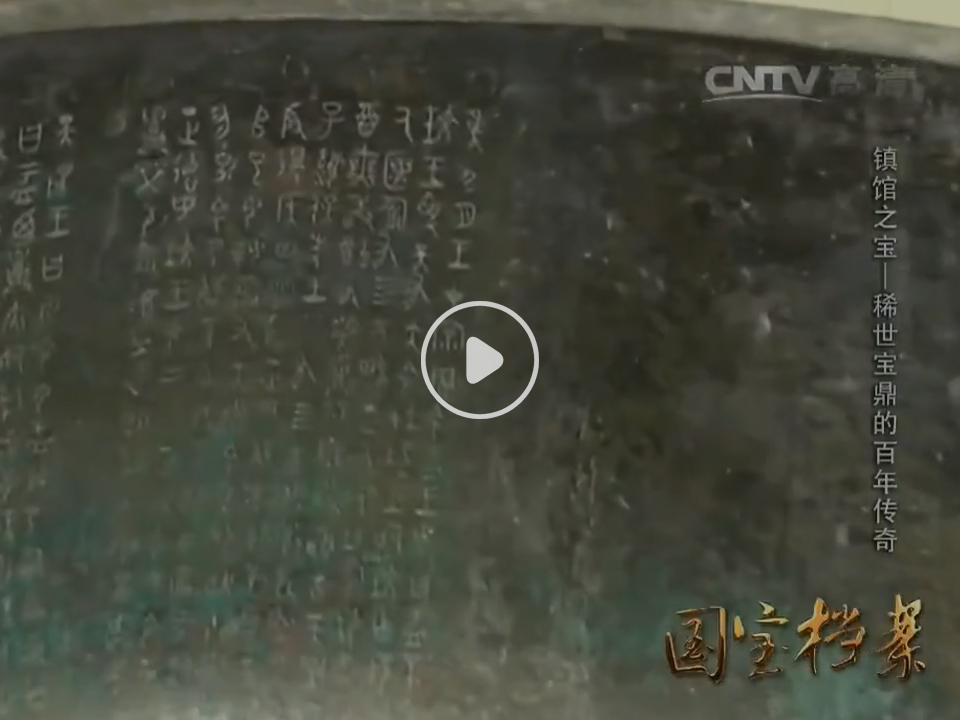



大克鼎铸造于公元前10世纪末的西周时期,距今已有3000年了。大克鼎威严厚重,口沿下装饰变形兽面纹,腹部宽大的纹饰波澜起伏而富有节奏感,蹄足上部饰有浮雕兽面。每组变形兽面纹间、足部的兽面纹鼻梁皆设宽厚的扉棱。纹饰线条凹凸、峻深,风格粗犷、质朴、简洁。商代晚期以来所形成的华丽、繁缛的青铜器装饰风格完全消逝。这种巨变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革。
鼎腹内壁铸铭文290字,铭文记载了作器者为“克”,他是管理周王饮食的官员,周王授予克的职责是上传下达王的命令。铭文内容分为两段,一是克对其祖师华父的称颂,二是详细记载了周王册命克的仪式以及赏赐的内容。这篇铭文是研究西周社会政治、经济的重要资料,也是西周书法艺术中的皇皇巨篇。
大克鼎于清光绪年间在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任村出土,具体出土的时间最晚不超过光绪十五年(1889年)年初。同出者尚有小鼎7件、镈、钟、盨等,皆为克所作之器,因此习称大鼎为大克鼎,小鼎为小克鼎。大克鼎出土后不久即为工部尚书潘祖荫所得,潘祖荫去世后,由其弟潘祖年运回苏州老家收藏。潘氏后人为保护大克鼎等珍宝费尽全力,特别是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主持潘氏家事的潘达于女士决定让大克鼎等再次入土埋藏,苏州沦陷后,先后有数批日军闯入潘家搜查,所幸的是始终没有找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潘达于女士决定无偿捐赠大克鼎和另一件国宝大盂鼎给国家。1952年上海博物馆成立,克鼎从此成为了上博最重要的“镇馆之宝”之一。